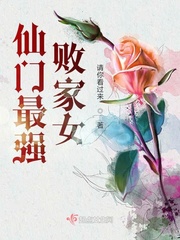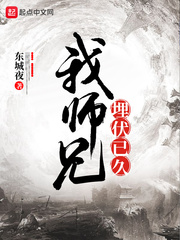第十五章:青灯照劣马,黄卷拭刀锋 (3-1)
司马嘉齐出身于一个名满天下的大家族——琅琊郡司马氏。
司马氏乃是天下经儒学派之泰山北斗,从学于其门下之弟子几可遍布六州,时人有“文归琅琊,武从泰阳”之逸说,可见其声望之高几可与武林霸主紫禁宫平起平坐。
世人皆称颂司马氏门庭之盛,却极少有人还记得,这样庞大的家族传承至今,也不过只经历了五代子嗣传续而已。
司马氏先祖名叫司马知玄,少时贫苦穷困,孤身起于青萍之末,百年前背井离乡来至琅琊郡,至此漂泊已近半生却仍是一事无成,望着琅琊郡衣冠辐辏、车水马龙的繁盛景象,他不由得暗下决心想要做出一番事业。
恰在此时,琅琊郡青松书馆开课讲学,司马知玄只听了一回便一发不可收拾,于是决定潜心修习经儒之学,头悬梁锥刺股,拜名师访高朋,苦学二十年间终成一代经儒宗师。集百家之长,修一身之德,颇有海纳百川之气象,他终是实现了当年的夙愿。
年过五旬,司马知玄自觉学问已有所成,便决定著书立说,开课讲经,将自己平生所学倾囊传授于有缘人,一时间慕名而来者竟是云集景从,险些踏断门槛,先后拜于门下学习之人总有千余之数。圣人云“五十而知天命”——司马知玄的“天命”便是家中的万卷藏书与座下的千余学子,他似乎已经窥破自己的余生之路,但从未有过半分犹疑。这条路注定孤寂乏味,他却是甘之如饴,无怨无悔。
司马知玄从贫苦拮据中冲出了一条血路,自然深知其中的艰辛滋味。故此虽已是从者如云万众敬仰,却仍守身持正端庄简朴,每餐不过一两道素菜,出门在外也只是布衣麻履轻车简行。宾客常常劝他,今日早已不同于往时,既然已经功成名就,何不放下矜持及时行乐呢?
每至此时,司马知玄总会微蹙眉锋,随后满脸严肃深沉地说道:“自古圣贤尽贫贱,我又岂敢有半分逾越?”
人总会有一些属于自己的坚持。
司马知玄有自己的坚持,他的长子也不例外。知玄生有三子,长子司马克仁,次子司马克礼,幼子司马克信。其中司马克仁乃是知玄贫苦颠沛之时所生,从小跟随父亲饱览世间炎凉,亦随父亲耳濡目染经史子集,胸中自有丘壑鳞甲,可性格却与父亲大相径庭,其父几十年如一日宛如苦修行者,司马门中一应事务,几乎皆付与司马克仁打理。
司马克仁受其父熏陶,平时不但治学严谨,处事更是心细如发。十六岁时接过家族执掌之大权,便已成为家族之中说一不二的大人物。司马一门从青萍微末走向门庭显赫,司马知玄的坚持与名望固然举足轻重,可一步步为家族的长久谋划搭桥铺路的却是司马克仁。
常言道长兄如父,每当司马知玄闭门修行之时,他就是家中的顶梁柱,一面替父亲掌管整个家族,修庭院、抚四邻、建学舍,一切都安排地如竹简编册般井井有条;一面将两位幼弟护庇于自己日渐丰满的羽翼之下,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全家长幼和睦美满。时人因此常有“生子当如司马郎”之慨叹。
待到司马克仁花甲之年,他深感自己时日已不算多,于是筹划着耗尽最后一口精气,为整个司马氏谋出一个安定无忧的未来。不久之后,他将族中德才兼备的子侄与学生细细遴选,送往天下各处势力以为辅弼,而各处势力自是欣然接纳。如此一直延续至今,就是那紫禁宫中当世三大智囊,除去为首的“病郎君”金不转之外,其余二位孔青山、孟修儒便皆是司马门下的学生。
因此,司马氏一门才得以在烽烟四起的江湖中站稳脚跟。
血脉流淌至今日,司马氏族中弟子已是第四辈,如今的族长名叫司马敬丘,受家学门风濡染,他将家族名誉看得极重。膝下亦有三子,名为司马审修、司马嘉齐与司马国芝,取修身、齐家、治国之谐音。长子与幼子皆是满腹经纶,胸藏锦绣,翩然有君子之风。唯有次子司马嘉齐自幼乖张顽劣,懒读诗书,平生只好与刀剑作伴,一壶酒一柄刀常做着江湖与沙场的幻梦。
沧海楼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百发小说网http://www.baifabohui.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是时候给女频一点震撼了
- 叶贺偶得一个游戏模拟器,游戏中可以模拟各种女频世界。<br 场景一:慕容红雪是手握二十万精兵的大将军,凯旋归来之后,被当朝皇帝发现是女儿身,然后就被一纸诏书直接赐死,慕容红雪留下一封血书后,含恨饮下鸩酒。<br 叶贺:赐死?谁赐谁?<br 老子要加九锡、冕十旒、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br 算了,太慢了,不够爽,直接杀进皇宫吧!<br 场景二:仙侠
- 5.0万字6个月前
- 玄浑道章
- 在世界经历了六个纪元后,天夏降临了………………玄浑道章书友群:【762873632】玄浑道章?造化之界:【526275426】…………......
- 744.5万字6个月前
- 从道兵开始修行
- 披甲执锐军中客,血枭营中一道兵。 风寒雨幕列成阵,沙场之中求道真! 我,徐瑾,是个道兵!
- 188.2万字6个月前
- 我在女尊世界修练茶艺
- 中土大陆,强者林立,众多家族势力盘踞一方。 “哎~” 房间中传来一声长叹,赵无忧十四年前来到了这个世界,在这里,人类煅练身体,与天斗与妖斗,他本以为开启了一段上天入地,神挡杀神,佛挡杀佛的强者之路。
- 82.0万字6个月前
- 仙门最强败家女
- 附身南梁朝第一修真豪门世家女纨绔,花宁洛醒来才知道,自己原来就是个走鸡斗狗,掀小姐姐裙子,踢寡妇家大门,臭名远扬的京城第一纨绔大混蛋,最关键的是身体原主竟然是死于偷看帅哥洗澡未遂! 花宁洛表示真的是没脸见人了,抱着破罐子破摔的想法,于是花宁洛在纨绔的道路上一骑绝尘…… 路人甲:“啊!花大少没死,花大少出门了……” 路人乙:“我靠,大家快跑啊……” 花宁洛:“额,怎么这么奏效吗?我这纨绔的功力还没
- 41.3万字6个月前
- 我师兄埋伏已久
- 西秦大陆,无数巅峰强者聚集。 “我师傅修为绝颠,纵横天下而未尝一败,谁知道他竟然在宗门秘境里被陆星河用数万个杀阵坑杀,我就想知道,我万剑宗秘境二十年一开,陆星河到底在里面埋伏了多久?” “我师兄是万年难遇的修炼天才,修为俯瞰世间,谁知道他竟然被陆星河联合绝世高手,然后用偷袭、用埋伏的方式斩杀,我与陆星河不共戴天。” “他明明修为如此高深,可是为什么还要用如此阴险,如此狡诈的方式埋伏别人.....
- 19.5万字6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