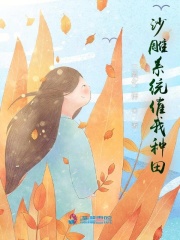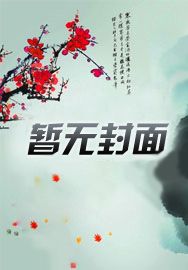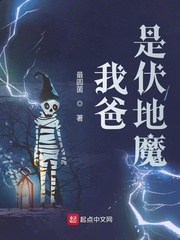第25章 乡有野贤 (3-2)
听得是本乡新任的有秩,那里监门又恭恭敬敬地拜了两拜,这才起身,低眉呵腰,道:“前日谢君走时,令人传谕诸亭、各里,君不日即来,命热拥慧相迎。本想着君还会再过几日才来,不意今就到了!谢君离任,乡民如群羊失主,无不惶然,不知相从,在闻君将来后,方才神主渐定,尽皆翘足相待,盼君早至。今君来也,乡民之幸。”
荀贞颇觉诧异,打量这里监门,心道:“一个监门竟有如此文辞?”问道,“你读过书么?”
“年少时读过乡学,后宣父辞官归里,教诲后生,人慕父德学,遂从学至今。”
“噢!原来你是宣父的弟子。”
“宣父门下数十百人,弟子只十人耳。人思钝愚笨,勉附骥尾为一门生而已。”
“亲授业者为弟子,转向传受者为门生”。弟子是亲传,门生是再传。一个饶精力是有限的,当门下弟子多时,做不到每一个都亲自面授,便只能再由弟子来代师授课。大儒郑玄最初投学拜入马融门下后就是“门生”,三年没有见过老师的面,只能听其弟子转相授业。
荀贞啧啧称奇。他对宣博的了解只限於其人经历,对其学问并不清楚,既然碰上了他门下的门生,便决定和这里监门多聊几句,问道:“你在宣父门下都学了什么?”
“父从师阳翟郭氏,精通杜律。人首学者便是此律。”
杜律是阳翟郭氏的家传。所谓“杜”,是和“大杜”相区分的。前汉武帝时杜周、杜延年父子先后任廷尉、御史大夫,皆明习法律,时人称杜周为大杜,杜延年为杜。此父子二人皆有律学传世,杜周所传是大杜律,杜延年所传即杜律。
“律”和“令”虽并称“律令”,但并不相同,是两种不同的法典。“律”是禁止法,是对犯饶惩戒法,是刑罚法典“令”是命令法,是行政法,是非刑罚法典。和“令”相比,“律”的权威性更高,更绝对,稳定性也较好,不容易变。
“律令”虽是面对全下人而定下的行为规范,但“律令”本身不会执法,执法者人也。是人就有不同,或宽仁、或严苛,“治狱有宽严”,即所谓“罪同而论议”。同一个罪行,所欲活就“附生议”,所欲陷就“予死比”。律令的比附解释不同,传习便呈现分歧,遂影章句”。
“章句”即“离章析句,求义明理”,本是读书人阅读古籍的一种分析方法,如春秋佣公羊章句、谷梁章句。借用到律学上,便出现了律章句,采用训诂学的方法分析汉律,阐发法制,大杜律和杜律就是这样产生的。
汉承秦制。有汉以来,对律法非常重视,前汉武帝“外儒而内法”,宣帝认为“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不可“纯任德教,用周政”。入本朝以来,虽儒家的学被传播得越来越广泛,但律法的地位仍十分重要,许多的律法名家都世代以明律法而出仕高官。
特别颍川这个地方,春秋属郑,后归韩,又成为韩国的都城和主要势力范围,从郑国时的子产铸刑书、立法制,到申不害在韩国的变法,再到韩非集发家思想之大成,又及汉初的郡人贾山、晁错、韩安国等极力推崇刑名法术,从而形成了“高仕宦,好文法”的社会风气,不少家族都是世代习律,阳翟郭氏、长社钟氏便是其中翘楚。
也因受这风气的影响,颍阴荀氏虽是儒门,是以儒学传家的,但当年荀贞从荀衢读书时,也学过律法,读过大杜律、杜律,虽谈不上精研,只是泛读,但对其也大略了解,当下随便举了个案例,让这里监门来按杜律来分析断案。
里监门稍一思考,侃侃回答,虽无新意,但断案本就不需出新,只要中规中距、公正平允就校荀贞越发惊叹,又问道:“杜律之外,你还学了什么?”
“父亦通诗,擅隶。人皆有学习。”
“噢?你学过诗?我且再考你一考,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出自何篇?是何意也?”
三国之最风流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百发小说网http://www.baifabohui.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快穿之不可以谈恋爱
- 丢失了自己逆鳞的小人鱼池谙,意外得知自己的真实身份原来是“反派拯救局”里的特派员,因为上次任务失误,而被消除了记忆。为了找回所有记忆,池谙重新踏上了任务之旅。但前提是不能谈恋爱。第一个世界,温柔的医生哥哥,池谙沦陷了。第二个世界,帅气的顶流弟弟,池谙屈服了。病娇血族、奶狗学霸、忠犬大佬……这谁顶得住啊?!接连的任务失败,池谙怀疑人生了。可随着最后一个任务目标的出现,池谙渐渐发现,事情似乎没有那么
- 12.4万字4个月前
- 沙雕系统催我种田
- 关右右打了三年工,公司突然宣布破产了。租了三年的房子,房东打电话说不租了,要求三天之内搬走。好不容易找到新工作,租到房子搬了家,去酒吧嗨了一个晚上,结果喝醉醒来穿越了。关右右:。。。好在临时绑定了系统,在末世种种田,打打怪,顺便收几个人做小弟,不过,这小弟头子看我的眼神好奇怪。关右右:他是不是暗恋我(???)乔化吉:我觉得不是。ps:事业文,感情线不多。pss:感情线真的不多??﹏??
- 12.7万字4个月前
- 次元探险:扮演瑞克,队友宝儿姐
- [[【飞卢小说网独家签约小说:次元探险:扮演瑞克,队友宝儿姐】这是一个拥有大量次元禁地的平行世界。穿越而来的江寒,参加了探秘次元禁地的节目,并开启扮演瑞克姥爷的系统。宝儿姐:“他负责坑,我负责埋。”小贱贱:“那一晚,我和姥爷合力狂砍81分。”理发师:“哇!!?…………哇?!!”观众:卧槽!这糟老头子怎么能这么强!?他怎么做到的?……江寒:不管你的问题是什么,答案都是因为我牛逼!飞卢小说网提醒您:
- 11.0万字4个月前
- 大唐:我国士天骄身份,被长乐曝光了
- [[【飞卢小说网独家签约小说:大唐:我国士天骄身份,被长乐曝光了】一朝穿越,成为了秦琼的脑疾之子,秦枫。与高阳公主竟然还有婚约。这对于秦枫来说,简直是天崩开局,他家里不缺绿原,不想绿的发光。因此,打算将计就计,继续装傻充愣,等高阳公主悔婚之后,再一展宏图!殊不知,一日天机泄露。秦枫天授至尊文武天才,终于再也苟不住了!“秦枫,我和你下棋,输了给你当娘子可好?”长乐公主。“得了吧,就你的棋艺,为何要
- 10.7万字4个月前
- 我爸是伏地魔
- 因为看不惯伏地魔有孩子这件事,路西被智障系统坑进了《哈利·波特》的世界。 而且穿成了伏地魔的亲儿子。 系统:本反派系统命令你,帮助伏地魔大人一统魔法界!成为最强反派! 路西:没问题。 系统:请完成进入斯莱特林学院的任务。 路西:一不小心进了格兰芬多,哎呀,我不是故意的。 系统:请和伏地魔大人开麦交流。 路西:*单方面脏话输出,交流完成。 系统:请帮伏地魔大人恢复身体。 路西:恢复成功!将伏地魔大
- 8.2万字3个月前
- 斗罗之药师传纪
- 我错过了万年之前的盛世,但这一次成神之路上必然有我的名字,而这片大陆上必将传颂我的名字。
- 18.1万字3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