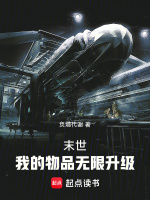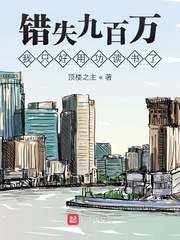第一部 迁移 第四章 (八) (3-1)
张平平受到的训诫大都来自杨二姊,杨二姊受到的训诫来自杨老爹、杨老娘,准格尔旗的亲戚熟人,张世良的爹娘、亲戚。进入九十年代时,同样聆听着祖辈训诫长大的南方人,零零星星地出现在包头旧城区的街道里,遇在一起时,他们就不停地用家乡话“哇里呱啦”。人生地不熟,沟通也不顺畅,初来乍到的他们都结伴生活,操着笨拙的南方普通话与本地人交流,本地人把他们一概称为南蛮子。
张平平初中的时候,巷尾的四十号院搬来个“小南蛮子”。
她会唱首叫《绣花鞋》的歌,老是表演给小孩儿们听。整首歌曲大家只听懂“绣花鞋”三个字,院里的小孩儿就管她叫“绣花鞋”。“绣花鞋”长得很有灵气,眼皮薄薄的,包裹着一对又黑又亮的大眼仁儿,齐齐的刘海乖乖地爬在额头,遮住她突出的奔儿喽,有时她把头发用皮筋扎成两个温顺的小辫子。她带副小眼镜,小孩儿们也喊她“四眼儿”。“绣花鞋”就是“四眼儿”,“四眼儿”就是“绣花鞋”,巷子里只有孩子们才明白的暗语有很多。
都只知道“四眼儿”是个“南蛮子”,但不知道她是南方哪个省的,在包头人眼里,出了内蒙都算南方。况且,绝大部分上岁数的人一辈子没走出过方圆百里,出市区就算是去过外地。比如杨二姊嘴里的“河南”,不是河南省,而是说黄河的南面。就算出门,最远就是去几十公里外的石拐区、固阳县,一辈子没坐过火车、汽车的大有人在,很多孩子直到上大学或者工作才头一次坐火车离开家乡。老辈儿人认识的外地人,基本是在解放前后迁徙或者流浪来的。解放前居多,比如家属大院里的邻居,就有山西忻州人,河北保定人,东北人,四川人,陕北人……都是解放前来的,社会稳定后城乡人口被固定在户籍中,很少有人口流动。
谁都无法预知,在未来三十年的生活中,天南海北不再是梦,日行千里成为真实。“四眼儿”们背着个“南蛮子”的标签,很快就跟当地人混得很熟。有时候,他们自己也会问当地人,你们管我们叫“南蛮子”是啥意思?“咿呀,谁能说清楚是个甚意思。就是外地人的意思哇!哈哈。”
“四眼儿”特别地机灵,适应本地生活比她家的大人快很多。她很快就喜欢上面食,爱吃土豆拌莜面,凉面皮、炒山药丸子,能大差不差地听明白当地话。让“绣花鞋”感觉最新鲜的是土炕,她从未见过睡觉的地方这么大。土炕是用黄土坯砌成的,家家都有,实惠好用,一般的炕上面能睡七八个人。炕的内部有烟道连接着墙里的烟洞,炕旁边连着一口烧饭的热灶,冬天的时候就在热灶做饭,把炕面烧得热乎乎的,家里温度也一起升高,正好取暖。夏天的时候不能在屋里烧饭,人们都在门口搭个冷灶做饭。这热灶挨着吃饭睡觉的地方,也有出危险的时候,听说有大人烧开水时没看住,把孩子掉到锅里。租房的人特意交待没见过炕的南方人,小心用火,可别出事儿。
“绣花鞋”家租的一间平房,一进屋是块空地,摆着桌椅和一个旧柜子,接着就是一张大炕,一家人都可以睡在上面,不像在老家,至少要三四张床。刚来的时候,她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到新奇。舀水瓢是铜的,还那么大,碗筷都比老家的大一圈。她又看到这里的窗户,上面是木头格子下面是玻璃,木头窗格子上糊着白麻纸,用手使劲一捅就会破,被她捅出好几个走风漏气的黑窟窿。
“绣花鞋”的语言天赋不错,很快就学会说本地话,还能用学来的土话骂人。院里的孩子喜欢拉帮结派,她跟哪个帮派关系都不错。然而,尽管她努力迎合,外来血统很难让她在本地当上孩子王——大概这是动物本性,她只能混个左右逢源。本地人多势众,当然是他们说了算。“四眼儿”有时带着她弟弟出来玩,她总是处处护着弟弟,害怕他听不懂这里的话被小孩欺负。
撒满星星的窟野河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百发小说网http://www.baifabohui.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末世:我的物品无限升级
- 太阳消失,异星虫群来袭,人类坠入黑暗时代。「劣质手枪lv1/9,伤害3,有效射程15米」累计造成十次有效伤害,可升级为:「普通手枪lv2/9,伤害4,有效射程30米,激活额外属性:子弹回复1/1h」面对来势汹汹漫天虫潮,林风获得物品升级系统,能让绑定装备,通过杀敌,累积升级点,实现装备无限升级。手枪→爆弹枪→核能炮……→歼星大炮升级还可获得额外属性:子弹回复,空间弹夹房车→装甲车→移动堡垒……→
- 82.6万字4个月前
- 错失九百万我只好用功读书了
- 家里拆迁,喜得九百万“巨款”。谁知刚实现财务自由,就重生了。杨旭站在2008年的烈日下,有些纠结。自己应该坐等十来年后,躺赚九百万?还是早早投身商界,搅动风云?看了看桌上标红的试卷,又看了看面前少女那双清澈眼眸里的点点星光。算了,先静下心来读书,顺便谈个恋爱吧。
- 8.6万字4个月前
- 人在木叶:开局抽到闪闪果实
- [[【飞卢小说网独家签约小说:人在木叶:开局抽到闪闪果实】白泽,前世顶级兵王,生前的唯一喜好居然是动漫。曾无数次幻想过穿越至动漫世界的场景,看着里面神乎其神的技能以及各种炫酷的能力,每次都让他热血沸腾。当这一天真的到来时,白泽张开双臂,仰天长啸!而当他开局直接抽到闪闪果实的时候,白泽:“所以开局既无敌?”当闪光与查克拉性质变化融合会出现怎样的变化?你能想象当拳头以超光速挥舞之时,所产生的威力有多
- 11.4万字4个月前
- 西游:开局吞噬金乌,亿万倍暴击
- [[【飞卢小说网独家签约小说:西游:开局吞噬金乌,亿万倍暴击】传说,上古大巫后羿射日,九只金乌散落大地化作九阳泉。而骊山温泉便为其中之一。“恭喜宿主,成功吞噬金乌遗骸”“触发百万倍暴击”“恭喜宿主,获得遁术金乌化虹”“恭喜宿主,获得天赋神通太阳真火”“恭喜宿主,获得大罗金仙修为”“恭喜宿主,获得功法金乌炼体术”“恭喜宿主,获得后天灵宝金乌羽扇”“恭喜宿主,获得扶桑桑葚*500”一朝穿越,赵元来到
- 10.8万字4个月前
- 人在奥特:这光之国不待也罢
- [[【飞卢小说网独家签约小说:人在奥特:这光之国不待也罢】一觉醒来,穿越到了M78星云,并且成为了传说中的极恶战士贝利亚。获得签到系统,首次签到就是海帕杰顿的模板。熟知枪打出头鸟的贝利亚,懂的了隐忍和低调。自此。光之国出了一个有名的谦和战士。凯恩:贝利亚,是一个非常值得信赖的朋友。玛丽:贝利亚,我希望您能带领光之国尽快走向辉煌。奥特之王:在我所认知的人里,只有贝利亚一人算得上真正的奥特战士。多年
- 8.7万字4个月前
- 打更人在一人世界
- 喇叭:“嗞嗞,喂!上面的同学请不要想不开人生的不如意总站十之八九。赌球害人远离世界杯。上面的同学~~-”夏禾:“我*!又是这个逗比,你们公司就没有别人了吗?!!”张楚岚:“这人谁啊?老子是被人绑架了,还有这种劝人活下来的调调是什么鬼啊!谁想不开了!”徐三:“。。。徐四你又干了什么!”宝宝:“撒子意思。”一人之下同人
- 11.6万字4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