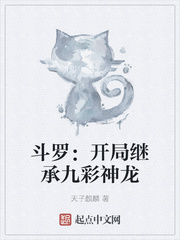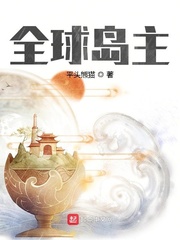第十六章 群起攻之 (3-2)
你姥姥的,从老夫口中探知西北边事,居然在皇上面前卖弄?回头看老夫怎么收拾你个痴愚。
数年前,英国公张懋得以提督十二团营军务后,在朝堂的话语权有所提升,底气也足了些,虽不再像以往那般唯唯诺诺,但“老好人”的姿态依旧。
说得好听些,他英国公张懋很会做人,难听点就是“墙头草”。
他不仅和宦官的关系不错,而且和文官也走得很近,从刚登科的翰林新人,到内阁大臣,他都愿意结交。要知道,他母亲的墓志铭,是出自内阁首辅徐溥之手。
不选择站边的他,无论是对文官还是宦官,都力求不得罪。
虽然“见风使舵”是他的本性,但甚少做“落井下石”之事。
陈璇自不可能知道张懋此刻心中所想,仍躬着身,恭敬地对弘治皇帝说道:“臣对西北边事仅略知一二。”
少顷,他又道:“今岁开春,马本兵与英国公至京营阅试,臣等洋相百出,实属罪该万死。皇上仁厚,宽宥臣等之罪,臣等铭感五内,遂发奋誓报浩荡皇恩。对马本兵之劝勉,臣等亦感激涕零。”
朱厚照听着陈璇浮夸的言语,嘴角微微一扯,暗道,拍我父皇的马屁也就罢,你这勋贵子弟,会感激马文升?除非太阳从西边升起来。
要知道,这班勋贵和马文升是有不少“新仇旧恨”的。
“新仇”就在陈璇所说的今岁开春。
那时马文升奉旨,与司礼监太监陈宽和英国公张懋等人阅试京营,结果一众侯伯、都督和把总真是令人“眼界大开”。
首试的是骑射,持弓不能发矢的有之,连弓拿不稳而掉地的亦有之。再问韬略,人人支吾,无法作答。
马文升怒而上请,要对十数名侯伯把总严加究治,从夺俸,到罢黜,再到逮问,各种惩处应有尽有。
而泰宁侯陈璇位列马文升奏请的严惩名单之首,这是“劝勉”么?
马文升这一举措,自然惹火了勋贵们。
“旧恨”则发生在弘治二年。
那年,马文升刚转任兵部尚书并提督团营,黜退不称职的将领有三十余人,其中不少人正是勋贵子弟。
这些年来,虽然勋贵对军务的参与有所提升,但能成长的勋贵子弟本就不多,整体实力是在不断下降的。
马文升这一黜退,无疑断了不少人的后路,遭到嫉恨是少不了。
于是有人持弓矢,半夜伏在马文升家门前欲暗算凶,未能得逞,遂又将诽谤信以箭射入东长安门内。
只不过为皇家效命而已,自身的生命安全竟受到威胁?
马文升自然吓得不轻,赶紧上疏乞休致仕,但弘治皇帝没有允准,“温旨慰留”之余,还派了十二名锦衣卫策其安全。
弘治皇帝礼遇有加之下,马文升没再坚持致仕,从六十余岁,又干到如今七十多。
泰宁侯陈璇顿了顿,又道:“皇上,保国公所率领的征虏军足有十万之众,北虏闻之,能不惧而退之么?”
朱厚照瞄了瞄陈璇,暗啧一声,北虏如此容易就被吓走?
他上一世所记载的史书里,有明一代,北虏对大明的侵扰可是自始至终都伴随着的。
想当初,太宗文皇帝五征漠北,也没有达到“漠北尘清”的目的。
第五次亲征回程之时,太宗文皇帝更病死于榆木川。
数次征战之后,大明的经济和军事不堪重负,国库已基本耗空,没法再进行大规模远征。
被五次征讨的北元残部虽然遭受重创,但随着大明无力再征讨,得到休养生息之机。
二十多年后,重新崛起的瓦剌部,就几乎给大明带去毁灭性的打击。
正统年间,听信谗言的英宗睿皇帝,居然效仿太宗文皇帝征讨漠北。
没有周密的战前部署,甚至连粮草补给还未备齐,在诏令下达的两日后,英宗睿皇帝统率的号称五十万的大军已匆匆出发。
厚照大明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百发小说网http://www.baifabohui.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生活向御兽师
- 我,林远,一名土生土长的蓝星人,机缘巧合下穿越到了一个神奇的御兽世界,本以为能够在这里干出一番事业,可惜造化弄人,我的第一只幻兽竟然觉醒出了一只扫帚精,从那天起,爷爷直接和我光速切割,路人对我百般嘲笑,从未见过面的未婚妻竟然直接拎了一个亿上门说再见!躺平多年的我决定不再摆烂,选择加入书架,查看我的逆袭计划……
- 12.3万字4个月前
- 惊奇的半岛
- 裴珠泫:“我真傻,真的,在他第一次喊我怒那的时候,我就该猜到他肯定是图谋已久了!”李在道:“怒那啊,我图谋的时间可比你想的还要久哦!”无力版简介:天才驱魔人的半岛故事!
- 10.5万字4个月前
- 仙武:我绑定了一个小说世界
- 李浩获得了一颗神奇的珠子,当他发现这珠子可以让他在仙武世界,和一个熟悉剧情的小说世界来回穿梭时。他悟了。仙武世界没有的,小说世界有!小说世界没有的,仙武世界有!两两结合,优势互补。他注定要在这里,建立功名,直冲巅峰!但一切的开始……不能成为血丹!ps:已经有二百万老书《全球高武之我的系统能氪金》,题材差不多,切勿错过。
- 18.0万字4个月前
- 斗罗:开局继承九彩神龙
- 【无敌文】重生斗罗大陆,开局就有三生武魂,而且其中一个还是九彩巨龙?完美转生的龙宸,注定要在斗罗大陆掀起一片腥风血雨。
- 14.2万字4个月前
- 全球岛主
- 王哲眨了一下眼睛,世界变了。 每个人头顶,都出现一座浮空岛。 只要念一句:“小小小!”,整个人就会变小进入浮空岛中。 浮空岛中有天大机遇,也有巨大风险。 很多人死在浮空岛中,也有不少人瞬间发达。 官方媒体发文:“岛中有风险,入岛需谨慎。” 王哲成了人见人爱的香饽饽,因为他不仅帅气逼人,还能看到提示语。
- 5.2万字4个月前
- 这小子明明很强却过分懒惰
- 当一个只会异能的家伙穿越了到了修真世界,然而……没搞错吧!你跑修真世界建立商业帝国!
- 6.1万字4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