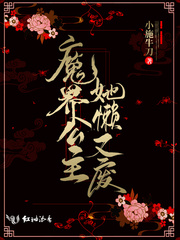任侠不可乱纪纲 (3-2)
独孤信点点头,微笑着继续说道:“‘士’虽然作为最底层的贵族,在分封初期不受统治者的重视与优待。但是他们大抵受过六艺之类的教育,成为诸侯争强称霸斗争中举足轻重的一支力量。在礼崩乐坏的时代,以往的等级秩序早已经无法维持,士阶层得此契机,得到了统治阶级的普遍重视。那时活跃于社会政治、军事、外交舞台的既有以研究学问、著书立说或设馆授徒而参与社会变革的学士;也有审时度势,藻饰辩辞,驰逐于天下的策士;还有专以武力事人的带剑之客。荀悦称之为三游,‘世有三游,德之贼也。一曰游侠,二曰游说,三曰游行’(《前汉纪》卷十)。荀悦指出‘游侠之本生于武毅,不挠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见危授命以救时难而济同类,以正行之者谓之武毅,其失之甚者至于为盗贼也’。侠是‘士’中的习武者,他们与学士、策士、术士的不同处在于,侠士勇决任气,常常以‘义’为出发点,以剑为行动的手段,参与社会活动。像曹沫执匕首为鲁劫齐桓公,专诸为公子光刺吴王僚,荆轲为燕太子丹刺秦王,以及信陵君窃符救赵所演出的侯嬴、朱亥的义举,无不以节义武力参与社会的政治活动。侠既为‘士’中一部分,就应该从春秋战国的土壤中寻找其产生的社会原因。太史公司马迁在《游侠列传》没有明确指出游侠产生的原因,但他认为国有困厄之时,人有急难之事。虞舜、伊尹等贤哲仁人尚遇困厄,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因而侠客之义是不可少的。这实际说明了侠与社会动乱的关系。”
杨逍此时插话了:“后汉史学家班固对‘侠’的论述比较明确:‘周室既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桓文之后,大夫世权,陪臣执命。陵夷至于战国,合纵连横,力政争疆。繇是列国公子,魏有信陵,赵有平原,齐有孟尝,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势,竞为游侠,鸡鸣狗盗,无不宾礼。而赵相虞卿弃国捐君,以周穷交魏齐之厄;信陵君魏无忌窃符矫命,戮将专师,以赴平原之急……于是背公死党之议成,守职奉之义废矣’(《汉书·游侠列传》)。班固强调天下失道,政在大夫,乱而生侠。”
独孤信道:“荀悦所作的《前汉纪》,不仅指出侠生于乱世,而且从儒家正统思想出发,认为侠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君昏民暗,纲纪废弛。他说:‘此三游者(游侠、游说、游行),乱之所由生也’。他还断言:‘凡此三游之作,生于季世,周秦之末尤其甚焉’(《前汉纪》卷十)。荀悦对游侠产生的社会原因的分析,应该说基本是合乎历史事实的。”
杨逍道:“不管是荀悦还是班固,他们对于‘侠’的认识,都是在大一统王朝初期社会对他们的普遍认识,可是随着人们越来越睿智,越来越有选择性,天下间的百姓们对于‘侠’的认识高度,那绝对不是他们二人的论断能够说得清楚的。”
独孤之后复孤独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百发小说网http://www.baifabohui.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我在苦境当前辈
- 素还真递给秦假仙一个锦囊。 素还真:Boss太强,打不过,看来是请出那位前辈的时候了! 秦假仙:那位前辈!难道是…… 素还真:不错,就是那位前辈,剑界不世传奇…… 秦假仙:等等,不应该是刀界顶峰再顶峰吗? 素还真:我们说的是同一位前辈吗? 秦假仙:你说呢
- 36.5万字5个月前
- 蜀地奇缘
- 叠最厚的甲,挨最毒的打。 任你出手快如风,我自不动安如钟。 敢为天下先,情字更在前。
- 10.0万字5个月前
- 让你代管宗门,全成仙了?
- 徐凡穿越,激活神级写作天赋。 本着苟到极致即躺赢的原则,徐凡轻易不与人起冲突,待人核善,远近无仇。 掌门远游,令徐凡代管门派教师妹修行,徐凡哪儿会管门派,面对师妹的请教,徐凡随手丢给了她们几本自己写的书,让她们去阅读。 师妹们在阅读这些小说后,一发不可收拾! “一念花开,君临天下!” “待到逆乱阴阳时,我以魔血染青天!” “仙路尽头谁为峰,一见无始道成空!” “手握日月摘星辰,世间无我这般人!”
- 10.1万字5个月前
- 觉醒仁君系统后,我的洪荒异变了
- 帝辛穿越洪荒,成了商纣王。 面对女娲庙的诗已经题了,妲己也要进宫了,自己距离死亡……也不远了的开局,他的心情沉重万分。 就在这个时候,仁君系统意外激活了,只要让对方认可自己是仁君,就能获得奖励! 从此,帝辛每天不是在感化嫔妃和朝臣,就是在向洪荒传播仁德的路上。 直到有一天,一道乌光冲天而起,世界剧烈震荡,系统突然要拉着帝辛一起沉睡…… “警告,警告,洪荒发生未知变故!系统启动紧急模式!即将沉睡!
- 10.8万字5个月前
- 天才绝艳莫师叔
- 主角莫凡因数年前的大战战胜剑魔,剑魔之妹苏清雅上山寻仇,却没想到遭遇与姐姐一样的失败。 而她失败的原因,竟是莫凡的天生异象。 天剑宗上下,尤其以掌门洛鸣羽最崇拜莫凡。 阴差阳错之下,莫凡成为人人口中的最强者。 对于这一点,莫凡已经懒得解释,然而新收的“关门”弟子,不断传出莫凡修为,以讹传讹之下,莫凡白日飞升...
- 41.2万字5个月前
- 魔界公主她懒又废
- 作为魔尊膝下唯一的公主,褚摇光前半生只想躺在魔宫里混吃等死,后半生只想躺在漂亮男人怀里混吃等死…… 他,“哪个漂亮男人?” 褚摇光哄道,“你。”
- 9.4万字5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