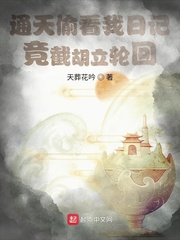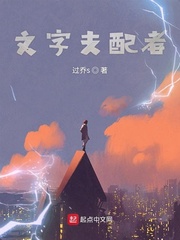第395章 收集资料 (3-3)
朱成山听到这话非常高兴:“长时间以来,西方国家只知道纳粹屠杀犹太人,不知道侵华日军在二战中曾经疯狂地屠杀中国人。国际舆论只谴责纳粹在二战中的暴行,很少抨击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中的暴行。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自二战胜利以来的几十年光阴中,在西方主流社会中有关日军侵华史实的宣传太少,声音太弱。如果我们能够有辛德勒的名单这样的电影,如果我们能够在国际上发声,日本右翼怎么可能这么猖狂”
张然用作保证的语气道:“我不敢说自己能拍出辛德勒的名单那样的电影,但我会竭尽全力,拍出一部经得起考验的电影,在全球发行。这也是张纯如的遗愿”
朱成山看着张然,想起了自己第一次见张纯如时的情形,同样是27岁,同样坚定而锐利的眼神。他就讲了起来,他第一次见到张纯如是在95年8月9日。当时他看着眼前时年27岁、漂亮但不会说汉语的张纯如,既为她的勇气而高兴,又不禁担心,这么年轻柔弱的女子,能否写好有分量的南京大屠杀作品
眼光锐利的张纯如似乎看出了朱成山的顾虑,把一本她当时以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为主题的作品蚕丝递给了朱成山,看到眼前这部厚似砖头、文字庄重、考证严谨的著作,朱成山的疑问一扫而光,随之取代的是感动。
朱成山当即表示将全力支持她,他不仅赠送给她全套的馆藏资料,而且,考虑到张纯如对南京大屠杀史料了解甚少,朱成山开了一长串的建议名单。
九年后的现在,张然获得了相同的待遇。朱馆长赠送给张然全套的馆藏资料,同时将几位在南京为张纯如提供帮助的专家,以及录像带中九位幸存者的地址告诉了张然。
按照朱馆长的指引,张然找到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王卫星和行政学院杨夏鸣教授,当初就是他们协助张纯如调查搜集资料的。张纯如在南京总共呆了25天。时间非常紧张,他们几个分头进行工作,王卫星收集整理资料,杨夏鸣陪同张纯如采访幸存者,采访工作结束后,再进行翻译。
在两位专家的回忆下,电影最重要的部分,张纯如在南京的经历在张然的脑子里慢慢清晰。
就在张然忙着收集资料的同时,第41届金马奖开幕了。未完待续。手机用户请浏览阅读,更优质的阅读体验。
电影教师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百发小说网http://www.baifabohui.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长生令
- 长生!从古至今上至帝王将相下到贩夫走卒谁不曾心存幻想古有秦始皇,东渡寻药曹孟德,摸金探秘唐太宗,行者问佛明太祖,屠龙掘脉明成祖,破浪西洋即便是末法时代依然有人在长生路上逐行如今天地灵苏,长生路现,人人可攀……到底是祸是福,是缘是劫?
- 12.7万字4个月前
- 直播画美金,粉丝怎么全是警察?
- 才艺主播苏文本想靠才华吃饭。但没想到,自从说自己擅长画画后,直播间里的老六观众死活要他画美金。没辙。为了讨好观众老爷们的开心,苏文被迫上班。就这样,随着他出神入化的画功下,一张比真钱还真的美金自他手中诞生。当美金出现的刹那。网友们不淡定了。“苏哥,变色油墨我来搞定!!”“苏哥,我能加入你们团伙吗?”“苏哥,我家开工厂的,有机器,能合伙吗?”而当网友纷纷玩梗时,下一秒,一个个警察冲进了直播间。“叮
- 5.0万字4个月前
- 人在零一:开局人生模拟器
- [[【飞卢小说网独家签约小说:人在零一:开局人生模拟器】飞电羽真穿越到了01世界,继承飞电集团。原本以为自己只能平凡过一生的他,却觉醒出骑士人生模拟系统。【当前可选择天赋为:半吊子硬汉侦探,肌肉笨蛋,老实人,天道总司才能。】【第一年:你作为飞电科技的社长,获得了假面骑士01驱动器。】【第二年:强大的天道总司天赋,让你以基础形态消灭了假面骑士迅。】【第四年:常磐庄吾十分欣赏你这个后辈,你成功从他的
- 10.7万字4个月前
- 遮天:我有一个加点面板
- 平凡青年穿越遮天获得一个可以给功法、境界加点的面板,从此人生不在平凡
- 13.2万字4个月前
- 通天偷看我日记,竟截胡立轮回!
- 叶知秋穿越洪荒,成为截教大师兄。却意外的绑定了的大道日记系统。每天写写日记就能变强!“书写日记,获得九转玄功!”“书写日记,获得大罗道果!”“书写日记,获得......”但是,未曾想到,系统居然有副本,被通天给捡到了。每天都能同步更新自己的日记。然后........“今日吾通天有感洪荒无数冤魂居无定所,祸乱世间,故此,立轮回,掌洪荒冥界地府,未央央众生再夺成道之机!”“轮回立!”后土带着巫族怒吼
- 23.9万字4个月前
- 文字支配者
- 意外获得了一本字典,在上面写下文字会拥有奇异能力。 写下剑字可以明悟剑法,成为侠客。 写下武字可以自悟武道,拳动山河。 写下雷字可以操纵雷霆,自比神明。 那写个仙字呢?
- 13.5万字4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