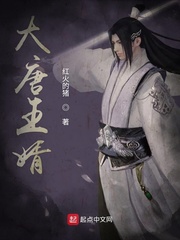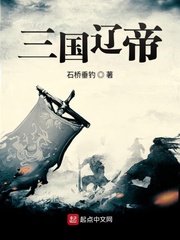第0030章 凌远的幸运 (2-2)
看着山坡上一垅垅翠绿,吴中行已经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为老师也为自己留住这个人,留住——他的心。
若是吴中行说些‘才学出众,可造之才’的话来,凌远还能回绝,可一句‘代凌大人凌夫人尽父母之责’说出来,他却除了感动什么理由也编不出了,喉间有些发涩,“凌远代父母弟妹谢先生”。凌远心中感动莫名,但他不知道的是,吴中行一路上心中暗叹侥幸,他凌远也该叹一声‘万幸’。
魂穿到几百年前的大明朝,虽是在心里做了诸多准备,但他毕竟生活在后世那个华夏民族历史上有史以来最为强盛的年代真正的盛世,哪里会体会到大明朝官场的黑暗,所遇到的大明官员,陆灏,李涤,陈大壮乃至徐国彦勉强还算得正直,更因为常斌这个当事人头脑清醒深知其中利害,他凌远才得保住性命甚至上达天听,否则他兄妹三人此时怕早已是山间的一堆黄土了。而眼前的这位吴中行吴大人,这时候他还没听说过这个名字,待他知道后至少也会感叹一声与有荣焉了。
吴中行,字子道,号复庵,南直隶常州府武进县人,嘉靖十九年(1540年)出生,隆庆五年(1571年)二甲第十八名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万历年间大明首辅张居正的得意门生之一。可就是他这位得意门生,在史书上都着墨颇多的万历五年张居正遭父丧夺情视事的所谓‘夺情’风波中,吴中行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他第一个上疏弹劾,把老师骂得差点气死,恼羞成怒又差点把他给打死,便是侥幸保住了一条命却也落下了残疾,过早地退出了官场。吴中行弹劾老师对与不对且另说,但至少说明他是一个正直的人,当时的张居正可谓权倾天下,敢上疏弹劾是需要绝大勇气的,何况弹劾对象还是他的老师。事实上他也的确算得上一个正直的人,若是换了张居正最得意的门生刘台过来,怕是凌远便没有这样的幸运了,至少不会对他这般上心这般看重一心要为老师留住他这个人才,更大的可能是暗地里捅刀子告黑状把他与张居正撕扯开,一脚踢开他这个可以预期的竞争对手争宠对象,肉体消灭的可能性都不敢说没有。
而吴中行虽是存了些许以后借为助力的心思,但更多的却是感激和欣赏,所以说凌远很幸运,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吴中行也很幸运,所谓因果当真不欺人半分。
“老师收你为弟子是因了此意,太后赐婚又何尝不是如此,太后亲自挑选聘礼,这天下也只有你凌远有这福分了”,吴中行点点头,目光却变得严厉,“但你可知你与方大人那一番窃窃私语,会为方大人及族人招来多大的祸事!”,李公公颁宣太后懿旨时,凌远与方三娘交头接耳他在身后如何看不见,虽不知他们说些什么,但其中利害他必须说清楚,否则不知以后还会生出什么事来,“往小里说,是蛮夷不知礼仪徒惹笑话。可要是落在有心人眼里,那便是她方大人心怀不满意欲抗旨了!”,见凌远张张嘴想要辩说,探过头压低了声音,“堂堂内阁首辅大人的弟子,难道还委屈她了不成?”。
吴中行只把这事往方三娘那边想,至多也只是想想二人乍闻喜讯有些失态而已,却压根就没往抗旨方面想,更不会想到要抗旨的正是眼前这位堂堂首辅大人的弟子。想了想又怕这番重话吓着了凌远,叹口气放缓了语气,“幸而左右皆为可信之人,李公公念你们没有此经历也只作没看见,但只此一次!以后可要仔细些”。
“是!凌远记下了,谢师兄提点”,一时激愤说出那些‘不合意撕了它便是,大不了咱们浪迹天涯去’的话来,若方三娘真是不愿意也就罢了,天下之大哪里去不得,管他身后洪水滔天。没料想竟是生出那般出人意料的效果,方三娘显是对小凌远早生情愫自是没有什么不愿意了,可这样一来那番行为便有些不妥当了。是以才有了后来拉着李公公亲热说话,又说了那些以他的性格在生人面前轻易不会说出口的话来,自是在做补救了。所谓言多必失,这个时候自是不愿多提,连忙岔开话去,“只是凌远才疏学浅,心中实是惶恐担心令先生失望”。
吴中行瞪了一眼立直了身子,“你家先生要我带话于你:安心温书便是”,顿了顿,“巴蜀豪杰地,川中多英才,不要老想着解元之事徒增烦扰”。
一本万历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百发小说网http://www.baifabohui.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特种兵之我前世是一名杀手
- [[【A级签约作品:特种兵之我前世是一名杀手】国际杀手榜排名第三的齐小白重生到了二十多年前,依然是那个熟悉的孤儿院。本来以为逃不过继续当杀手的命运,却没有想到,在五岁时,被一单亲母亲收养。有了光明正大的身份,有了在阳光下生活的机会,齐小白自然不想再回归黑暗。只是,自己的养母叫张海燕,还有个小了两岁的妹妹叫叶寸心?好吧,她们的未来,由我来守护!(本故事及人物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切勿模仿。
- 12.2万字5个月前
- 大明皇叔
- 只是吐槽了下作者,眨眼间发现自己竟然穿越了…… 等等,我没想穿越啊! 竟然成了历史上鼎鼎有名的作死王——朱高煦! 造反的话,关键现在是永乐二年…… 那么当务之急就是先把老爹、大哥巴结好,顺便开始跑路吧,京城太危险,我要去云南! 谁知这一跑,跑出个新世界……
- 90.4万字4个月前
- 大唐王婿
- 一不小心,来到了贞观初年,莫欺少年穷的剧本? 不好意思,拿错了。
- 3.9万字4个月前
- 三国辽帝
- 来到汉末成为张辽。今生我不会再傍大腿,我要用并州铁骑一统十三州,建立大辽国!
- 5.2万字4个月前
- 温水煮三国
- 一千个人心里,就有一千种三国幻想。 中平六年,主角无意中走入乱世三国。 主角:我只想找到正确的打开方式!
- 9.8万字4个月前
- 重生罗成之将星入命
- 军校大学生到了古朴、原始、真实的大隋唐,重生罗成,他可不做累人的皇帝梦,只想纯纯粹粹、干干净净的上阵杀敌,和三军将士露天席地,大口喝酒痛快吃肉,当个最爽将军。堂堂天下,敌军来犯,生死看淡,不服就干!杀杀杀!三十斤的陌刀我舞动如飞,穿五十斤重甲,马亦被甲,冲入敌阵刀枪丛林,拿四米长的马槊把敌将挑飞,咱有“将威”!当将军做兵仙,留美名成佳话!如李靖般著兵法,比李绩还出将入相,他带着军事博物馆,星戒让
- 9.4万字4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