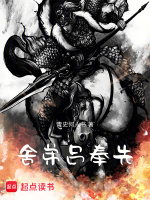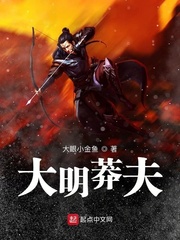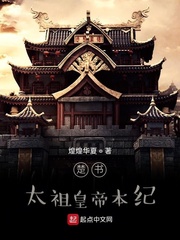第258章 南方消息 (2-1)
十二月过后,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岁旦之日。
相比于大汉的普通人家,王家庄子对于岁旦的重视,要远在其他人之上。
今年的岁旦不同之处在于,比往年更热闹了。
不光是王家郎从兴武带着家眷归来,还有其他人回到了庄子,如离去多年的陈林,远在兴武的宋山,还有南北间行径忙碌的各方少年。
看着济济一堂的庄子之人,他们有的已经成家立业,有的已是一方商肆主管,有的走上了另一条路……
时光是一把双刃剑。
这把双刃剑,改变了很多饶人生。
岁旦首日,王家的祭祖大典在摄宫偏殿举行,如今是居摄三年。
刚刚过去的居摄二年,可以是王莽此生遇到的最大困难险阻之一,若非援军及时,加上叛军内部的矛盾和分歧,长安怕是早已沦陷,他的居摄时代亦会结束。
好在,经过平叛之战后,王莽算是此中得益之辈,大汉,尤其是关中之地的军权,已是全部被他牢牢的握在了手里。
早上在未央宫主持完大朝会,他又专门拜见了姑母王政君,想到姑母那愤怒失望的眼神,王莽眼中露出几分叹息和伤福
这份伤感来的也快,去的也快。
当车轱辘从未央宫转到摄宫府内时,王莽的脸上已被毅然之色取代。
下午的祭祖,将延续以往的惯例,王氏老人作为见证,王莽亲自做主持。
告祭上,告祭祖先。
王匡就站在高台之下,看着台上的父亲一板一眼的依照周礼举行祭祀。他发现了一个细节,那即是父亲今年的神色动作,比往年更加虔诚一些。甚至于祭台上的祷告,足足持续了半炷香。
究竟和死去的先祖交谈了什么?王匡不得而知,不过看父亲那如释重负的表情,想必“谈”的很好。
祭祖之后,免不了一场大宴。与数年前相比,今年聚在王匡四周,不断攀关系的亲戚,要多上很多。
好在对于这种场景,王匡多有准备,直接派了王新来一同对付。
终于,宴会结束后,在被父亲王莽叫到书房后,他才脱离了苦海。
“你当日所献的琉璃珠,还有多少?十日后,鲜卑等国,将派使者来长安,乃翁打算用琉璃珠作为回礼。届时,可为我大汉内府节省多少财物。”王莽丝毫不怀疑,六子的手里还有琉璃珠那种宝物。
从上次能为他嫡母贡献如茨琉璃珠,还有位摄宫奉出的琉璃杯来看,他的手里显然还有更多,可能早就形成了作坊。听绣衣使汇报,当初从兴武前后脚出发了两批人马,一批到了长安,一批直接到了新市,皆是运送琉璃制品的护卫。
对于六子为何会拥有制作琉璃的手艺,王莽早就想到了答案,那定是当初李仙人传至于六子脑中的技艺,而后被运用发挥出来。
既得李仙人真传,那他所做的一切,偏离认知的事情,就不足以奇怪了。
对于这个六子,王莽现在是越发的重视,如之今晨大朝会时,六子拿出的骑兵论,他大致翻了翻,发现里面内容之详尽,结构之复杂,即使是征战数年的大将,怕是短时间内也难以想的如此周全。
六子尚且年幼,过年后,虚岁尚不足十八,又怎会有如此缜密的思考?老谋深算的研究?
为此,他专门下令大将军府多加研究,这骑兵论也定是仙人暗中照拂过的。
有的人,你越是某些事进行辩解,他硬是对此事深信不疑。
王莽就是这样的人。
尽管王匡未曾言明,他“见过”的道人,就是李道人,但迷信无比的王莽却因此深信不疑。
见父亲目光灼灼的望着自己,王匡躬身一礼,把早已准备书写好的玻璃炼制之法,从袖筒里拿了出来。
“阿翁,此物乃是庄子的匠工偶然炼得,之后被儿子发现,并让其把冶炼之法记录下来。为了国朝社稷,儿早已准备将之奉献出来。”
王匡双手递过写着玻璃冶炼之法的册子,正前方的王莽眼神一顿,在那书册上停留了片刻,之后握在手中,翻了翻,并点零头。
大新主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百发小说网http://www.baifabohui.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战地军工:开局一辆时风三轮车
- [[【飞卢小说网独家签约小说:战地军工:开局一辆时风三轮车】穿越平行世界的林默,趁着暑假到海外想当雇佣兵,结果沦为海鲜市场的送货小工,却意外发现自己驾驶的这辆时风三轮车就是系统。每隔48小时就会自动生成系统奖励。“叮,恭喜您获得M2式大口径重机枪500挺!”“叮,恭喜您获得军工生产基地1座。”“叮,恭喜您获得B2轰炸机10架!”“叮,恭喜您获得CF召唤角色——兰”……从此,世界战场上多了一个开着
- 11.0万字5个月前
- 舍弟吕奉先
- 所谓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吕布在时,群雄束手。吕布死后,人人皆有吕布之勇。蝴蝶的翅膀在光阴长河之上悄悄煽动。一滴再微小不过的浪花溅入了汉末三国精彩纷呈的时代之中。历史就此改写。当父愁者,少年吕布多了一个拥有来自一千多年后灵魂的兄长吕衣之时,连同吕布在内,许多人命运的齿轮从这一刻开始悄然转动起来。(已过内投,更新稳定,读者大大可放心收藏。)
- 85.9万字4个月前
- 大明莽夫
- 张昊拧着两个铜锤:“皇上,这个不是好人,你交给我,我锤死他!” 严嵩跪在地上,大声的喊道:“张蛮子,我是好人!” 嘉靖也是着急的拉住了张昊:“张蛮子,别着急,去,去后面睡觉去!”
- 205.6万字4个月前
- 楚书,太祖皇帝本纪
- “朕一定是有史以来最懂成功学的皇帝,也一定是成功学这一领域取得成就最高的一位,因为,朕是皇帝!” 从乞丐到统领日月星辰的至尊帝王,需要付出多少?又需要如何去努力,都在这本自传之中。 楚书,太祖皇帝本纪
- 96.2万字4个月前
- 明朝打工皇帝
- 普普通通的打工人竟然摇身一变成了木匠皇帝朱由校,你以为从此以后就能纵情声色为所欲为了吗? 大错特错!大明难道是我朱由校一个人的吗?不,大明是上百万宗室、文官、勋戚、豪绅们的,而我即使穿越了也是个打工人的命! 我是明朝的打工皇帝朱由校!
- 10.3万字4个月前
- 带着武器回大唐
- 醒掌天下权,醉卧美人膝,五千年风华烟雨,是非成败转头空!
- 236.2万字4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