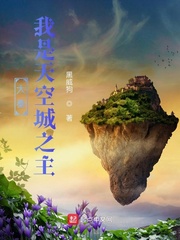第95章 夤夜访逢纪 (3-2)
逢纪迫不及待地拿出一卷,小心翼翼地展开,看着书册上的篆体读道:“公食大夫之礼。使大夫戒,各以其爵。上介出请,入告。三辞。宾出,拜辱。大夫不答拜,将命。宾再拜稽首。大夫还,宾不拜送,遂从之。宾朝服即位于大门外,如聘。”
而在书卷所录的正文旁边,又用小字隶书密密麻麻地注释了许多条目,比如“使大夫戒,各以其爵。”的旁边就注了“戒犹告也。告之必使同班,敌者易以相亲敬。”
无论是大字篆书正文还是小字隶书注文的字迹都朴素古雅,一笔一划自成天地方圆,绝非粗制滥造之俗物。
逢纪一目十行地翻看过去,只见卷末处写着“牟平刘祖荣注,愚侄德远敬录”几个大字,顿时喜上眉梢道:“还真是故太尉所注之书,难得!难得啊!”
颜良见逢纪如此神态,心知自己挑的这份礼物算是挑对了,也不枉自己在刘延面前做了回恶人讹诈了来这些书籍。
古今中外,无论是什么国度,什么年代,知识永远是最高的财富。
而掌握知识的人,便有机会从“劳力者治于人”转变为“劳心者治人”,从“治于人者食人”转变为“治人者食于人”,通俗来讲就是有机会当官。
书籍作为知识的载体,便成为了各家各族所珍视的传家宝,等闲不可示人。
书籍的珍贵,固然有持有者希望知识的传承不轻易外传的原因,也有当前时代载体的限制。
两汉之时,纸张虽然已经被发明了出来,但此时的制造工艺尚且很落后。
即便本朝著名宦者蔡伦曾进一步改良造纸工艺,制出了名满天下的“蔡侯纸”,汉和帝也下令推广纸张的应用,但此时的纸张仍旧只是豪族显宦手中的奢侈品,尚且达不到替代竹简木牍的程度。
纸张没有普及,印刷更是无从谈起,书籍的传播便只能在原始的竹简上手工传抄。
要说到颜良拿出来的这一套《仪礼》本身,与《周礼》、《礼记》合称为三礼,其流传的范围倒是不小,但这类传承自春秋时的典籍跨越的时间久远,文意古奥难明,非寻常人能够轻松解读其含义,所以便需要各大学问家来为这些典籍做注释。
像当代的大学问家郑玄就曾注过包含三礼在内的许多典籍,当然,每个稍有底蕴的家族家传的典籍都各有不同的注释。
为面前的这一套《仪礼》的做注的人乃是东莱牟平人刘宠字祖荣,历仕九卿、三公,更是当世鼎鼎有名的清廉贤臣。
曾经有一次,他从会稽太守的任上被调入朝中任职,山野间有几个白发老叟听闻消息后专程来为刘宠践行,每人皆持百钱程仪略表心意,刘宠固辞不受,问父老为何如此。
老翁们答曰:“山谷鄙生,未尝识郡朝。它守时吏。发求民间,至夜不绝,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车以来,狗不夜吠,民不见吏。年老遭值圣明,今闻当见弃去。故自己奉送。”
刘宠叹道:“吾政何能及公言邪?勤苦父老!”
为了不拂了老翁们的一片好意,又实在不愿意受百姓的钱财,只好从诸老叟手中各取一枚钱收下。
刘宠的这般清廉作风,为其赢得了“一钱太守”的美名,载誉天下。
虽然像逢纪这般对于迎来送往觉得理所当然的人,自然是不会去效仿刘宠的清廉,但这并不妨碍他仰慕刘宠将三公挨个儿做了个遍的显赫经历。
能得到当代宗室重臣亲自注释的家传典籍,岂不让逢纪如获至宝。
逢纪分别拿起几卷一一看过,然后小心翼翼地放回锦盒,说道:“祖荣公学问精深,怕是我也非一时半刻可以通读领会,这……”
颜良所说的向逢纪请教自然也是托词,立刻接着话头道:“自是如此,不若这些书卷就留在先生手边,待先生通读之后,良再一一向先生请教,如何?”
逢纪颔首捋须,笑眯眯地道:“此议甚妥,立善有心了。”
颜良心道我当然有心了,孔乙己曾曰过“窃书不算偷”,那自己赠书当然也不算行赇,咱这是风雅事,和那些伸手就掏出金银珠宝的粗鲁家伙可不在一个档次上。
三国求生手册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百发小说网http://www.baifabohui.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特种兵:神级辅助
- [[【A级签约作品:特种兵:神级辅助】曾经的百战老兵黑色贝雷帽成员,现如今的瘸腿小学门卫,看着电视机内的祖国70周年阅兵,他老泪纵,横。当上天再次给他一次机会,来到特种兵的世界,睁开眼睛就是正在看莎士比亚文集的庄焱,他又将何去何从。且看一个百战老兵如何将一个个年轻愣头青一步步的调教成最强大的战士。(本书单女主,不种马还请放心品尝)【著伟大的祖国母亲70周年生日快乐】(本故事及人物纯属虚构,如有雷
- 10.7万字5个月前
- 三国:成亲就送特殊兵种
- [[【A级签约作品:三国:成亲就送特殊兵种】穿越三国,激活最强兵种系统。只要成亲,就奖励特殊兵种。燕云十八骑、八百骠骑、五百飞虎军、一千兰陵军团、三千玄甲军、五千陌刀手、七千白袍军、八千背嵬军……白起的虎狼之师!霸王项羽的八千江东子弟!百战穿甲兵、黄金火骑兵……历代精锐兵种,皆入麾下听从调遣,开局就杀的异族心惊胆寒、惶惶如丧家之犬!曹操:“苏宇麾下猛将何其多也!”袁绍:“世间贤臣良将,为何皆入你
- 11.1万字5个月前
- 大秦之秦皇子婴
- [[【A级签约作品:大秦之秦皇子婴】他败刘邦灭项羽,六合归一!他败曹操灭刘备,横扫三国!他败杨广灭李渊,隋唐称雄!他灭女真吞北宋,铁骑无敌!他败蒙古吞南宋,世界震惊!他吞明朝灭鞑靼,保卫文明!他不是别人,正是被人称为暴君、明君的大秦三世皇帝一一嬴子婴!(本故事及人物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切勿模仿。)]
- 10.5万字5个月前
- 大秦:我是天空城之主
- 我叫叶轩,是这座天空城的主人,你要问我怎么得到天空城的,我只能告诉你,我就是睡了一觉而已。 不过当我带着天空城出现的时候,终有一群人跪在地上,高呼什么仙人和天人的之类的。 至于我的天空城中有什么,那就真的不谈了。我的城卫军能以一当千,我还有亩产十万斤的百亩良田,美若天仙的侍女,反正你能想到我这里有,你想不到的,我这里也有
- 8.4万字4个月前
- 战疫之守护我的城
- 写在武汉封城后的故事。林清平是光明社区的一名网格员,他的故事从撞开一扇门开始,而那一天的时间是2020年1月23日。PS:因为作者君身在武汉,所以想写一些看到的听到的小故事。读者交流+薪盟VIP群:450416188(全..
- 18.0万字4个月前
- 新瓦岗
- 新瓦岗 四猛:罗士信,来护儿,新文礼,王伯当 四绝:罗春,尚师徒,侯君集,程咬金 十三杰:李元霸,宇文成都,裴元庆,雄阔海,伍云召,东方伯,伍天锡,罗成,杨林,魏文通,梁师泰,杨义臣,秦琼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自己的四猛四绝和十三杰人选,这是甜城心中的选择,希望大家能喜欢,《新瓦岗》这是一个不一样的隋唐英雄传!
- 211.3万字4个月前